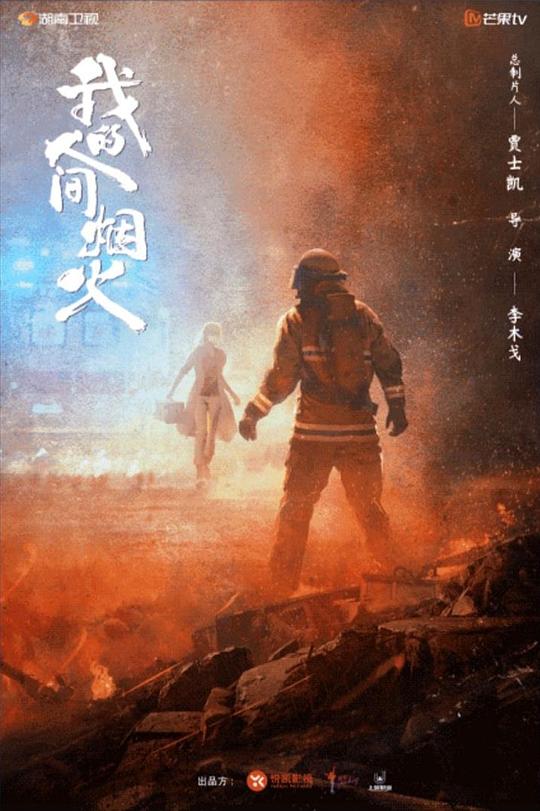花开山乡正片
- 第1集
- 第2集
- 第3集
- 第4集
- 第5集
- 第6集
- 第7集
- 第8集
- 第9集
- 第10集
- 第11集
- 第12集
- 第13集
- 第14集
- 第15集
- 第16集
- 第17集
- 第18集
- 第19集
- 第20集
- 第21集
- 第22集
- 第23集
- 第24集
- 第25集
- 第26集
- 第27集
- 第28集
- 第29集
- 第30集
- 第31集
- 第32集
- 第33集
- 第34集完结
J资源访问比较快,不卡,影视线路友好
《花开山乡》推荐同类型的国产电视剧
《花开山乡》同主演作品
剧情/介绍
有些情况下,可以适当使用一些方言,不然很出戏。王雷的演技还没曹云金这个渣好。单位组织看的,但是发现这部剧很好看,充满正能量,祝祖国越来越好王雷的演技从来没让我失望过,现在又碰到这种适合自己的剧,挺好的。反应当代农民的真实生活,很接地气的作品,曹云金王雷演的很真实
年轻时,她的家就是山脚下的一片草原,一张单人床,一颗蓝色的树,树上挂满风铃,照片,布娃娃;年轻的时候他们三个的理想,是一起去乡下教书;年轻的时候会用17种语言说我爱你;年轻的时候每年拍一段录像带,收录年华,纪念青春;年轻的时候,欢子的想念里可以有两个人,高举是一双眼睛,而张扬,张扬是一个孩子;年轻的时候他俩甚至可以忘记爱情的排他性,坚信欢子是属于他们两个人的,年轻的电影可以让无关紧要的人是塑料模特,大海外可以是鱼缸。
年轻时,发过许许多多的誓言,最后一个发在毕业时,说三个人不再相识不再见面。可是正如张扬说的,一个人遵守诺言的最好方法是让自己不再是那个人。但是他始终相信,欢子和高举会在外面的世界再次相遇,要不然,诺言也没有了意义。而他自己选择在不离开双秀园一号,那个欢子离开了的家,那个等着欢子,那个有效期50年的“有求必应”卡来找他的地方。这就像年少时真心爱着我们的恋人,他们说,没关系,虽然你离开我,但如果有天你会回头,我依然在原地守候。
他们违背誓言了吗?高举摇头。呵呵,因为他已经改名叫高乐,他已经不是原来那个人。发了誓就能忘记一切吗?
虽然发誓不再提起从前,可是,爱,正如高晓松所说,就像我们手指间流过的那些叫做岁月的东西一样,偶尔还会涌上心头。
我不知道高晓松是不是刻意截取了达利的影子:电影中反复出现的那幅广告牌,是周迅的一幅巨大照片分割后的不规则拼凑。让我想起达利给自己的挚友洛尔卡作肖像的手法,两者如出一辙。这幅画改变了肖像的意义。
我们对往昔的追忆,也许就像这幅画一样,那些脸庞被肢解,事件被颠倒了顺序,刻骨铭心的全是一些支离破碎的片断。他们丝毫不会削减记忆的美丽,就像一块块的肖像中,我们分别辨认出来的各部分都是完美的,真是的。而到了电影尾声,那幅广告牌被按正确顺序重新拼起来之后,反倒失真了。正如王朔在《动物凶猛》的开头中说,描写多年后的于北蓓,完全失去了记忆中狐狸般的俏丽风姿。这就是记忆的失真。于是我才真正理解了米兰.昆德拉说的那句话:记忆不是对遗忘的否定,记忆只是遗忘的一种形势。
梦,就是在现实的重重打磨过滤之下,失去了朦胧的底色。所以清醒之后做出来的艺术叫做现实主义,而表现主义,只能是梦境中的甜美和苦涩。
七十年代出生的人都拥有漫长的青春期。高晓松是一个永远在做梦的人。有一天看高晓松的访谈,谈起从小家境优越,大学时,为了体会什么是苦难,背着吉他去“讨饭”,流浪到天津大学被扭送到校长室,给家里打了个电话,表哥开车来接他,告诉他说卖唱讨饭然后打电话我就来接你了,这就是苦难?告诉你,苦难是没有尽头的东西,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摆脱,那才是苦难。
他自己也说,世界上第一个在盆子上画画儿的人一定吃饱了,第一个在山洞壁上作画的人一定觉得很暖和,第一个在海边唱歌的人一定打到了鱼。人满足了所以才做梦。
上天也有宠儿,他让大部分的纨绔子弟不学无术空活百岁,却也赋予了少数一些人一辈子做梦的能力。高晓松可以对每一个他爱过的人说,没有钱,我就背着吉他带着你去流浪,我们坐着火车浪迹天涯,他可以在看到美丽的河流时得意忘形地把仅有的一双鞋脱下来扔进水里,他可以半夜三更爬上长城,可以醉酒后跳进干枯的水库游泳摔得鼻青脸肿,他说,人站在那里应该把自己看成一道风景。
听他说这些话时,我微笑地想起她的电影里,高举说,我们要沿着长城一直走,能走多远走多远,然后在那儿露营,想起高举把未经许可的拜访说成到一个美丽的山脚下放风筝,然后和一个不期而遇的漂亮女孩一起玩游戏,想起欢子固执的说,那条船是来接我的!
正如我的影碟封套上写的那样,《那时花开》不是你打开窗能看到的风景,而是你在歌声中闭上双眼脑海里色彩斑斓的灿烂和忧愁。那是早上你来过留下过弥漫过的樱花香,是倾城的月光,是记忆中那些盛放在头发里的花儿。
青春亦如草稿般的草草了事,可我看到《那时花开》,看到稚嫩的脸,看到结尾处夕阳的映衬下,蓝色的树在燃烧,女孩伫立远方,山川庄严温柔,朴树在浅浅地唱那首《那些花儿》......我掉下眼泪,知道原来年轻真的那么美,只为电影对青春的一次誉写。为逝去的岁月永远留恋,为手中的年华提醒幸福,这样的美丽已经足够,何须深究它的表现主义是不是称得上“试验”,算不算得上“A-G”?觉得美就已经可以了,因为那也正是对青春一词最好的诠释
若从线性叙事的角度来说,可能更容易一点。在高举大三那年,张扬从西安退学回到北京,两个人组建了一个乐队,住起了上下铺。在迎新的时候,遇见了欢子。欢子和张扬在一起了,却约定她只在星期一到星期五属于张扬,星期六她属于高举,而星期天她谁都不属于。三人一起愉快地度过了欢子的大学生活,约定从此以后互相不认识,如果谁违背了誓言,就要去死。(但是毕业以后,张扬还是和欢子结婚了,之后又离了婚。)高举重新以高乐的身份追求欢子,就在两人即将结婚的时候,欢子发现自己怀孕了。高举为了逼问孩子究竟是谁的,终于承认自己违背了誓言。于是欢子和高举决定一同赴死。临死时,他们再约定,如果第二天醒来发现两人没有死,就结婚。然后他们就结婚了。
在整个线性的故事当中,只有括号里的部分最模糊,因为我们只能通过零散的镜头语言来判断这一事实。电影采用了黑白默片的形式,连两人的对话,都是以全屏字幕的方式出现,以此区别于其他彩色的部分。然而,却只有这一段是真实的,其他的所有,都仅存在于离婚后的张扬所写的那个叫做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的小说中。
这在片中有许多证据,比如当高举以高乐的身份出现时,两人的对话被完整地记录在了张扬的word文档上;再比如高举终于与欢子确立恋爱关系的那天,他在海里游泳,海水的边缘却是张扬的鱼缸;再再比如高举和欢子每次看电影,电影院上排的那个放映员永远都是张扬。张扬在二人的故事中是一个全知全能的存在。高举与欢子是张扬的剧中剧。
可我在开篇便说,这“本来”是一个剧中剧。是的,倘若影片就此展开并结束,它本来是一个剧中剧。但是在最后,我们却发现,欢子的视角也被插入了进来。影片开头划起的那根火柴,到最后被欢子用来焚毁象征她内心世界的山脚小屋。而在火焰中,她与高举与张扬的两次婚礼,分别以彩色和黑白的形式交替出现,让人仿佛以为这一切的一切只是欢子一个人的回忆(甚至幻想)。那么故事就具备了另一种叙述的可能性——
是欢子虚构了这一切吗?就像大雨之夜,欢子与高举拥吻,被闯入的张扬看到,那时身为张扬女朋友的欢子仍未停止,只是一边与张扬对视,一边继续拥吻。张扬在整个故事中,也只是个观看的角色吗?
然而就如影片所说,“看电影的人被自己看了,像一个悠长等待的结果是时间未曾流逝,成长是忘了提问的回答。回忆比幻想还不真实,电影比爱情更忠于我们。”
张扬和欢子在长城郊游时与高举走失了三天,高举却以为是整整一年。他在这悠长等待的过程中,实验着自己的毕业课题,可结果却是时间并未流逝。对于毕业课题长达一年的访谈讨论,与张扬欢子口中言之凿凿的三天,到底哪个才是真实的?
连叙述者自己,都忘了去找寻答案。
可仍然有些小细节,无论回忆也好幻想也好,在不真实的叙事中昭显角色的可靠。比如关于诺言。
三人的第一个诺言,是欢子的归属问题。欢子星期一至五归张扬,星期六归高举,星期天归自己。但是他们都违背了这个诺言。张扬是一个简单粗暴的人,他在星期天闯入时,欢子问为什么,他说,“星期天我也要你”。
而高举却只能迂回的方式假装偶遇。他说,“咱们并没有说过星期天不许到一个美丽的山脚下来放风筝啊”。
这大概也就预示着他们对最后一个诺言的态度。他们的最后一个诺言是假装从此以后互不认识。可是张扬与欢子在影片一开始便突兀成婚,完全不需要理由;高举却通过了种种方式,改变姓名,以此逃避对违背诺言的自责。
是细节赋予了故事的可靠性,而绝非叙述本身。或许是因为记忆本来就该是失真的、细碎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往往愿意无数次回想过去的点滴,却很少有人愿意真正回到过去再重新经历一遍。倘若失去了无限种叙述的可能性,那么记忆便不再是记忆了。
多年前我第一次看这个片子,写过这么一段话,“它只能用来感觉,好像天空落下沙砾似的雪,噼里啪啦全部打在心上;一下子很疼,然后很冷,然后过了很久很久,暖成水,又哗哗地流掉。”
现在读来,有些年轻时候的矫情。可是正是这种矫情,比记忆更可靠地提示了曾经的观影体验。并且我可耻地发现,多年过去了,我的观影体验并没有新的改变。
“开始的开始,是我们唱歌。最后的最后,是我们在走”。
“那些飘满雪的冬天,那个不带伞的少年,那句被门挡住的誓言,那串被雪覆盖的再见。”
“生活是无法被记录的,但可以被歌唱,我们要歌唱了”。
关于《那时花开》,我想写很多东西,比如有求必应卡,比如塑料模特的意旨,比如长城走失的不同解读,比如小站的假面舞会,比如高举的长衫,比如张扬的玩具手枪,比如片中向无数经典电影的致敬。
可是这一切,都如我多年前所写的那样,更适合用来感觉。就像上文那罗列的三段歌词/台词,需要我们用自身的回忆和幻想去填满。若导演本不想叙述一个老实完整的故事,那么我的解读其实并无意义。
青年干部白朗从中央机关下派到芈月山村任第一书记,他带领全体村民,将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的实际结合起来,兴办一系列新型产业,终于冲破重重阻力,闯出了一条致富之路,谱写了一曲乡村发展的振兴之歌。